老轨检修发电机,被齿轮压断一截手指,想想就疼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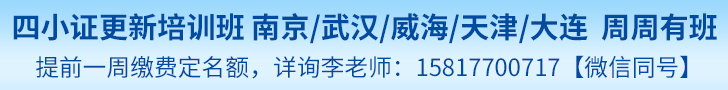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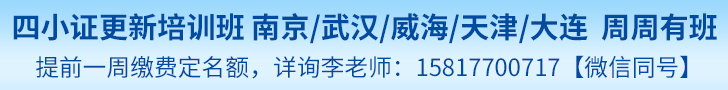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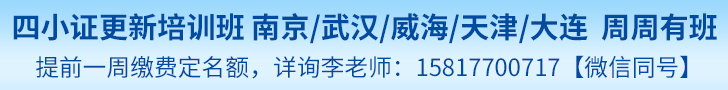


三副小证有Z01基本安全Z02精通艇阀Z04高级消防更新 ,有效期5年,到期前参加到校3天培训,就可......
课程安排 开班时间:2025年7月25日考试时间:一般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就可以回家培训时长:都是3天......
培训内容与必要性本次更新班涵盖两大核心项目: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培训合格证更新(简称Z02更新)与基......
连云港四小证更新2025年6月 四小证更新 Z01基本安全Z02精通艇阀Z04高级消防每周三开班,周......
《船员条例》第二十五条和二十七条分别规定,船员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、法规按照国家有关规......
作为一名有7年航海经验的远洋船员,目前我已经干到船长的职位了,就在去年我果断选择了转行。之所以选择转......

报名条件:1.要求具有初中及高中【含中专、技校】以上学历,无色盲、色弱、无传染病、口吃、痞足、肝功能......
作为一名远洋船员,很负责任的说海员这个职业的离婚率确实很高。我去年工作的那条船,船上有二十三名船员,......
船员合格证更新四小证证书有效期多长时间?船员证书到期怎么换新?...
2021海员(2年海员健康证)体检定点医院...


船员证书5年到期更换需根据证书类型和失效时间选择知识更新培训、考试或重新培训,具体流程分为有效期内、失效1年内和失效......

海员证是海员的必备证件,国际海员和国内航线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海员证,可是海员证是有效期的,有效期5年。到期前需要更新换证,......

报到地点:华洋海员培训中心【每周三开班报名微信:hxhy991】 报名条件1需要提前查询证书符合条件就是培训学员原合格证......

上课时间2025-08-04报名详询李老师:15817700717【微信同号】培训时长一般3天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就可以回......

课程安排上课时间2025-08-04报名详询李老师:15817700717【微信同号】培训时长一般3天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......

课程安排上课时间2025-08-04报名详询李老师:15817700717【微信同号】培训时长一般3天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......

课程安排上课时间2025-08-04报名详询李老师:15817700717【微信同号】培训时长一般3天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......

上课时间2025-08-04报名详询李老师:15817700717【微信同号】培训时长一般3天是当天中午学完考试就可以回......

四小证更新2025年8月4日 Z01基本安全Z02精通艇阀Z04高级消防更新 11规则课程安排上课时间2025-08-0......

四小证Z01基本安全、Z02精通救生艇阀和救助艇、Z04高级消防、T06客滚证,有效期5年,到期前需要参加到校3天再有效......

